“公共必修课”有两个概念,一个是“公共课”,一个是“必修课”。“必修课”是一个教育行政管理概念,上者教育部,下者学校,规定某门课为必修,关键在教育部。
我们先回顾一下大学语文的简要历史。大学语文的前身是“大学国文”,“大学国文”是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伊始就有的一门高校公共必修课。中国现代语文学科创建于1904年的“癸卯学制”,早在学制酝酿期间便已确定要有这样一门课。1902年张之洞致电管学大臣张百熙说:“中国文章不可不讲。自高等小学至大学,皆宜专设一门。”到正式形成《高等学堂章程》和《大学堂章程》,便都有了这一门课。课程命名之初,除“中国文章”,还曾叫“中国文学”,是“中国文章之学”的意思,再后来简称为“国文”,在大学也就是“大学国文”。大学堂里文科专门学堂也有一门“中国文学”课,那才是与今天“中国文学”意义相当的课,两者不可以混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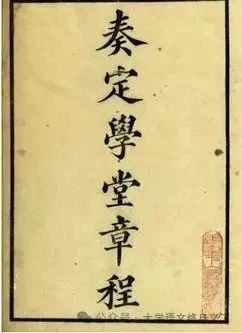
“癸卯学制”的“高等学堂”相当于大学预科,“大学堂”相当于大学本科,这门课开始为大学预科必修课,大学本科选修课,所以又曾叫做“预科国文”。后来大学预科取消,预科里的一些课程归到本科一年级,便成了“大一国文”——这已是1922年以后的事了。
回到1912年,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,成立了中华民国,第二年即1913年民国教育部颁布《大学规程》,仍然规定大学预科国文为公共必修课。1922年实行新学制(即“壬戌学制”),取消大学预科,大学预科国文遂演变成“大一国文”。1929年民国教育部重新颁布《大学规程》,再次确定“大一国文”为各专业公共必修课,这是最早从制度上的规定。1931年,民国教育部《修正专科学校规程》第8条规定:“各科专科学校以党义、军事训练、国文、外国文为共同必修科目。”1938年,民国教育部整理大学科目,明确规定“国文及外国文为基本工具科目,在第一学年终了时,应举行严格考试。国文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及作通顺文字”,“至达上述标准,始得毕业。”所以,民国“大一国文”一直是大学各专业的公共必修课。

这一状况到1949年才发生变化,这一年5月6日,北京大学新校务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,决定调整课程:大一国文改为选修,大一学生及文法学院二、三年级学生为了学习新开设的课程,可以退选若干旧课程等。1950年1月,清华大学校制商讨委员会讨论学制及课程改革问题,也取消了“以前同学所认为不合理的和不需要的如大一国文、英文、测量、水力实验等课”。由此启动了大陆内地高校取消大学语文课的多米诺骨牌效应。这是学生绑架了教育行政,不能作为大学语文应该必修还是取消的依据。重开大学语文课后,也有不少面向学生的问卷调查:“你喜不喜欢这门课?”“你认为这门课应不应该开?”这都是错误的,误导学生以为这门课是可以凭兴趣学或不学的,我们应该吸取当年取消大学语文的教训。
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国大陆内地高校重开大学语文课,1996年国家教委高教司在全国组编本《大学语文》“出版前言”中指出:“大学语文是普通高校中面向文(汉语言文学专业除外)、理、工、农、医、外语、艺术、财经、政法、教育等各专业学生开设的一门素质教育课。课程的目的是培养学生汉语语言文学方面阅读欣赏理解与表达能力。这是大学生的文化素质教育中的重要方面。”2006年9月,国家发布“十一五”时期文化发展规划纲要,提出“高等学校要创造条件,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中国语文课”。2006年11月,教育部高等学校中国语言文学学科教指委在湖南文理学院召开“高等学校大学语文教学改革研讨会”,会议形成“纪要”,建议教育部把大学语文作为全体大学生的公共必修课来开。2007年,教育部高教司以38号文件(函)的形式转发这个纪要。2008年,教育部国家语委发布《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(2007)》,其中列有“高校母语教育”专题,对2007年的大学语文状况作出详细描述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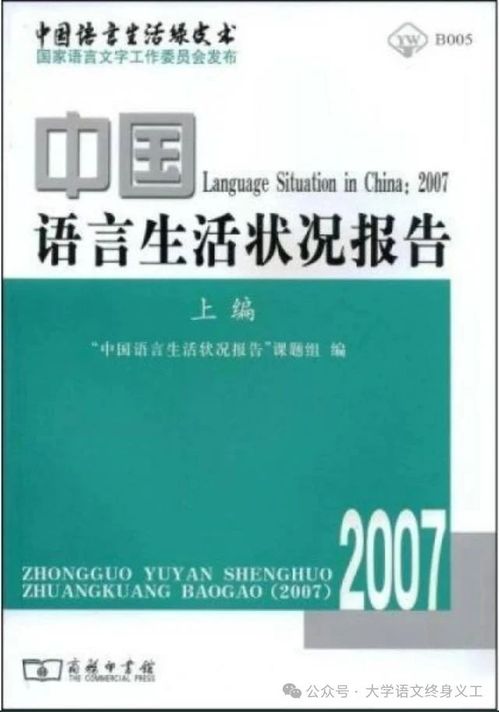
2018年,教育部发布《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》(简称《新国标》),经济学、金融学、经济与贸易、政治学、社会学、马克思主义理论、大气科学(应用气象学)、图书情报与档案管理(档案学专业)、旅游管理等九大专业,都规定必修或必选大学语文课。高等职业学校大学语文是大学语文的半壁江山,2019年教育部发布《关于职业院校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制订与实施工作的指导意见》,规定高等职业学校应当将语文课列为必修课或限定选修课。但是教育部始终未发文规定高校所有专业必修大学语文课,按教育部的解释,“因为高等学校课程设置的问题涉及高校办学自主权,教育部并没有做硬性规定,该课程设置由学校自己决定。”这就使这门课程究竟是否应该必修蒙上了一些不确定因素。
港台方面,1949年后港台高校延续了民国学制,仍然规定“大学国文”为公共必修科目,但也并非一帆风顺,譬如香港高校的本科教育一度实行英式三年制,这就把大学国文等一些公共课给挤掉了。而台湾高校的大学国文课也在1995年被台湾“司法院”大法官会议宣告“违宪”,自此是否必修成为各大学自行决定的事情,有些学校仍然必修,也有的学校停开,更多学校则将其纳入通识教育课,台湾高校的大学国文课陷入混乱状态。港台的乱象是有特殊背景的,大陆内地高校的大学语文课应该以此为戒。大学语文是最重要的一门母语高等教育课,是统一大业的重要一环,我们必须从这样的高度来看待这门课的必修或选修问题。
再谈第二个概念,即大学语文是高校的一门公共课。高校课程分为专业课、公共课和通识教育课三大块,其中通识教育主要就是选修课,因此,大学语文是公共课还是通识教育课,这个归属关系很大。公共课是各专业必修的,语文“听说读写”的能力是各专业学习都必备的能力,所以应该是公共基础课。通识教育是沟通各专业的课程,譬如文科学生要懂一点理科知识,理科学生也要懂一点文科知识,是可以进行选修的。假如把大学语文归入通识教育课,那么下一步就必然发生“必修改选修”的事情。还有一个区别,就是语文“听说读写”是一种能力训练,而通识教育课则侧重于知识性,尽管它的本意不仅仅是知识,外语词源也不仅仅指向知识,但是翻译到中国,“通识”一词的指向就是知识性的,往往就是“通用知识”的意思,事实上很多高校的通识教育课也都上成了知识性的“概论课”,可谓是名副其实。这个问题目前我们注意不够,很多高校把大学语文纳入通识教育课,就是教育部2018年编制的《新国标》,对于大学语文的归属也摇摆不定,在明确须开设这门课的九大专业系列中,有5个专业归为“通识教育课程”,4个专业归为“公共必修课程”或“学科基础知识课程”。这个问题要及早解决,否则会危及大学语文必修课的地位。
来源:“大学语文终身义工”微信公众号
2025年6月2日 14:22 海南